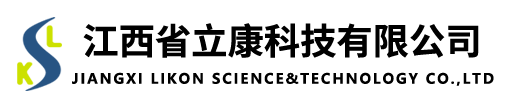銀錢細(xì)流
賬簿攤開(kāi)在榆木桌上,壓著一把算盤,珠子油亮如墨玉。我常坐于此,點(diǎn)數(shù)銀錢的涓滴。這銀錢,向來(lái)有它自己的品性,不喜喧嘩,亦厭惡奢靡,只向著那精細(xì)處流淌。
所謂理財(cái),初時(shí)不過(guò)是數(shù)點(diǎn)進(jìn)出,后來(lái)竟?jié)u漸顯出它的紋理來(lái)。每一文錢都似有了生命,在指間躍動(dòng),訴說(shuō)它的來(lái)龍去脈。我于是明白,銀錢亦如溪流,疏導(dǎo)得法便灌溉田畝,任其橫流則成澤國(guó)。那數(shù)字的排列,看似枯燥,實(shí)則內(nèi)里有大文章。增與減之間,隱約可見(jiàn)興衰之兆;盈與虧之際,分明藏著治亂之機(jī)。
先前只道銀錢事是俗務(wù),后來(lái)方知不然。一厘一毫的計(jì)較,竟能照見(jiàn)心性的明暗。揮霍者未必豪爽,儉省者未必吝嗇。銀錢流過(guò)掌心,留下的不只是銅臭,更是一種心性的刻痕。我見(jiàn)過(guò)富室因放縱而敗落,也見(jiàn)過(guò)寒門因節(jié)制而興旺。銀錢原是無(wú)情物,卻在人手中生出萬(wàn)千氣象。
銀錢事小,關(guān)乎心性事大。流水不腐,戶樞不蠹,財(cái)務(wù)亦然。每一筆收支記下,不獨(dú)為盤點(diǎn)存余,更是為明日蓄力。那數(shù)字的累積,原是為了減去不必要的負(fù)累,增添有意義的留存。
算盤聲停,賬簿合攏。銀錢細(xì)流仍在暗中流淌,只是從此有了方向。
這方向不是別的,正是向著那“效”字而去。效者,功倍事半之謂也。昔人云:“磨刀不誤砍柴工”,今我乃知:理賬不誤生財(cái)?shù)馈C恳晃腻X安置得當(dāng),便如良將布陣,各司其職,各盡其用。冗余之處,自當(dāng)削去;不足之地,理應(yīng)補(bǔ)全。銀錢排列既整,事業(yè)自然亨通。
我漸覺(jué)察,理財(cái)之道,實(shí)則與治水同源。大禹疏浚九河,不是一味堵截,而是導(dǎo)其流向,分其湍急。財(cái)務(wù)亦然,不是錙銖必較的吝嗇,而是讓銀錢流向該去之處。該花費(fèi)處,縱千金也不當(dāng)吝惜;該節(jié)省處,雖毫厘亦不可輕擲。這其中分寸,非精于計(jì)算者不能把握。
提質(zhì)二字,尤在“質(zhì)”上做文章。質(zhì)者,本也,根也。銀錢往來(lái),表面是數(shù)字增減,內(nèi)里卻是價(jià)值的交換。以微薄之資,獲豐厚之益,這便是質(zhì)的提升。如同匠人琢玉,不是多用力氣,而是巧施技藝,使頑石成器,使常物生輝。財(cái)務(wù)之質(zhì),在于使每一文錢都發(fā)揮其最大效用,不至于沉睡箱底,不至于虛擲無(wú)用。
常聞人言“開(kāi)源節(jié)流”,卻少有人思及開(kāi)源與節(jié)流之間的關(guān)聯(lián)。開(kāi)源不是盲目擴(kuò)張,節(jié)流也不是一味緊縮。如同人體呼吸,一呼一吸間自有節(jié)奏。財(cái)務(wù)之道,在于找到這個(gè)節(jié)奏——何時(shí)該投入,何時(shí)該回收;何處該慷慨,何處該儉省。這種節(jié)奏感,需在日復(fù)一日的計(jì)算中慢慢體悟。
夜幕垂降,我仍獨(dú)對(duì)賬冊(cè)。燈花偶爾爆響,仿佛應(yīng)和著算珠的輕吟。這些數(shù)字不再是冰冷的符號(hào),而是一個(gè)個(gè)生命的軌跡。它們記錄著清晨購(gòu)入的米面,正午支付的工錢,傍晚售出的貨物。每一筆都是一個(gè)故事,每一次計(jì)算都是對(duì)故事的梳理和升華。
我忽然明白,精細(xì)化財(cái)務(wù)管理,實(shí)則是在經(jīng)營(yíng)一種生活態(tài)度。它要求人既看到森林,也不忽視樹(shù)木;既把握大局,也關(guān)注細(xì)節(jié)。這種態(tài)度不僅適用于銀錢事務(wù),更可推及人生萬(wàn)事。一個(gè)人若能如此經(jīng)營(yíng)財(cái)務(wù),大抵也能如此經(jīng)營(yíng)人生:不浪費(fèi)時(shí)光,不虛耗精力,不做無(wú)益的投資,不進(jìn)行無(wú)效的付出。
銀錢如水,能載舟亦能覆舟;管理如舵,能導(dǎo)流亦能定向。在這細(xì)流般的計(jì)算中,我看到的不僅是銀錢的增值,更是自我心性的提升。每一個(gè)數(shù)字的確認(rèn),每一次收支的平衡,都在無(wú)聲地塑造著一個(gè)更加精細(xì)、更加高效的生命形態(tài)。
銀錢細(xì)流終入江海,而江海不拒細(xì)流,故能成其深。(劉皓東 仇瑞焓)